B05黃聖系友
以色列初印象
當飛機抵達特拉維夫,隨即從本古里安機場搭乘鐵路前往海法。由於身上行李較多,我待在車廂出口附近。行經數站後,一位年紀約莫三十上下的姊姊氣喘吁吁的跑進車廂,待火車啟動後不多久便主動和我搭話。她問我是第一次來以色列嗎?我告訴她,我第一次來以色列是在我高一的寒假,當時我的父親在魏茲曼科學院作訪問學者。其實那時參訪了諾貝爾獎得主的實驗室,看見以色列科學家用樸實的實驗器材作出改變世界的研究,就默默地在心中種下來以色列求學的種子。然後她也和我分享自己的人生歷程,她雖然是在美國長大,但因著猶太血統決定回到祖國生活工作,起初只是抱持著嘗試的態度,經過幾年後她決定永久的移民到以色列。於是我就好奇的追問,究竟是甚麼緣故讓她決定留在以色列生活?這個問題讓她思索了一會,然後意味深長的說,我是因為這裡的「人」才決定留下來生活。她接著解釋,以色列是個很特殊的國家,常常發生很多令人意外的事情。當時剛好火車忽然停止。不是到站了,也沒有廣播說明情況,我們就沒有來由地停在軌道上。她笑了笑說,以色列就是現在這樣,常常發生意想不到之事。有時候是更殘酷的,人們寶貴的性命可能在一瞬間就永遠的失去了。然而就是因著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,以色列人並不會太在意所謂不重要的事情,反而很珍惜家人朋友,甚至與路上陌生人的相遇。只要主動請求幫忙,一定會感受到以色列人的善意。揮手和她分別後,我不禁思考,我以往所認為重要的事物,像是學業表現、工作待遇等等,其實在死亡面前一點也不重要。但是在身旁的家人朋友需要時伸出援手,或者向路上遇見的陌生人表達善意溫暖,這些似乎是更重要且彌足珍貴的。經過一番長途旅程,我在以色列理工的求學正式開始了。

█ 剛抵達以色列本古里安國際機場
以色列修課心得
我曾經在以色列市場買菜時,和當地人閒聊。當他們聽見我正在就讀以色列理工,便露出一種複雜的表情:一面覺得欽佩,一面也透露出你大概很辛苦吧的意味。我起初並沒有那麼明白,而是在修課一段時間開始寫作業之後,才慢慢體會到箇中滋味。我發現,課程中所指派的作業,往往是在教授對於課程內容十分深入的理解下而自行產出的,因此在一般的文獻或課本中不一定能找到相對應的資料。在第一次寫這種難度的作業時,我孤軍奮戰,結果不但花很多時間,效果也沒有那麼顯著。後來慢慢地摸索下,我發現面對這種艱困的作業,最好的方式就是找教授同學討論。當然,這和我以往在大學時期的學習方式不太一樣。現在我必須推翻我以往不求於人的堅持,學習主動聯絡教授和同學尋求幫助。當我這麼做時,其實也沒有一下子就解決問題。因為教授只會提點一些方向,而同學們也和我一樣解不太出來。但是,老師的提示就像燈塔,讓我在風暴的海上還保有希望;同學們並肩作戰的態度也激勵著我不放棄繼續往前。這些過程讓我想到古代富有盛名的以色列國王所羅門曾經說過:「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,因為二人勞碌,可得美好的酬報;…有人能打勝孤身一人,若有二人便能抵擋他;三股合成的繩子,不容易折斷。」(聖經,傳道書,第四章)。將近三千年前的話語,體現在現今以色列理工的課堂之中。這種團結互助或許就是歷史上猶太人成功的秘訣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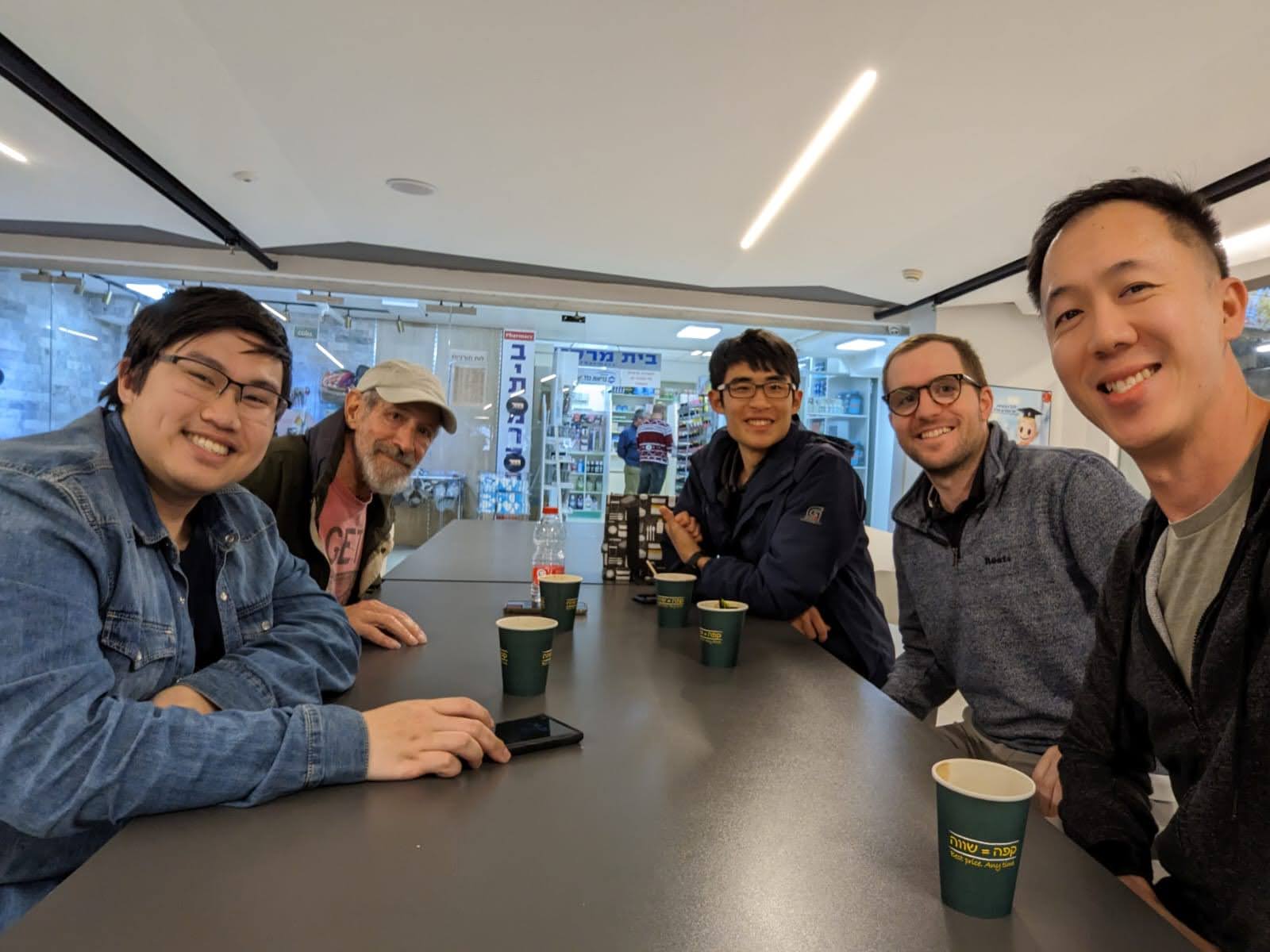
█ 和同學朋友在校園裡喝咖啡(右三)
以色列學術研究感想
最後,想分享一點在以色列作研究的心得。正如上方所述,我父親曾經在以色列作研究,有一點是令他很震驚的:這裡的教授和學生互動和東方很不一樣,學生是可以質疑甚至衝撞教授的。這和我們東方文化背景滿不一樣,我們很講究倫理道德,尊師重道,長幼有序;以色列文化比較直接,學生勇於質疑批判,老師也滿習慣這種碰撞。我在這裡和教授作研究討論的過程中的確體會到這一點。說實在的,我並沒有特別習慣這種互動模式,但這種互動方式的確會加速彼此的溝通,進而更快的解決問題。並且這也說出了學者尋求真理的態度。二戰後,愛因斯坦在柏林創立第一個以色列理工學院學會並擔任其主席。他曾經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演講說過他對於教育的看法:「有時,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作一種工具,靠它來把最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。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。知識是死的,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。它應當在青年人中發展那些有益於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。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消滅個性,使個人變成僅僅是社會的工具,像一隻蜜蜂或螞蟻那樣。因為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統一規格的人所組成的社會,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。相反,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,這些人把為社會服務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問題。」我相信,正是如此直接的互動方式並尋求真理的態度,以色列才會培養出許多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,為自己的國家甚至世界作出貢獻。 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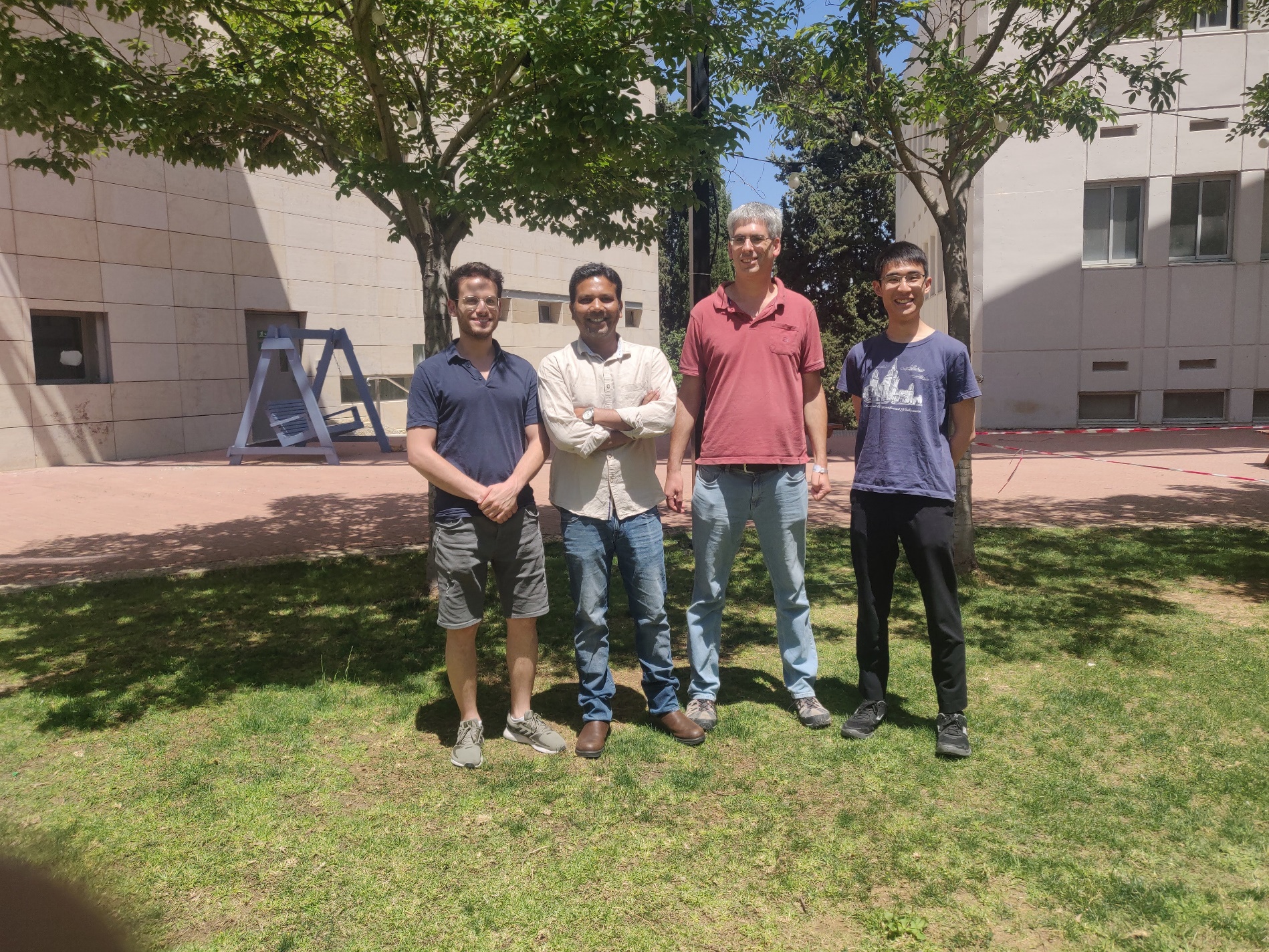
█ 與指導教授和實驗室成員合照(右一)
作者簡介:
黃聖,台大機械學士B05級畢業,目前在以色列理工學院Technion就讀機械所。若同學有興趣來以色列理工交換或唸學位,歡迎來信聯絡我:b05501112@ntu.edu.tw
點閱人數